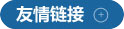(家强按:此文写于1996年的冬天,收录于我在2000年出版的第一部个人作品集子《经历韶华》。今天很偶然地重新翻看到,写作这篇文章的那个冬天,如在目前)
一
那一年,我刚刚二十岁,充满热情与迷惘的年龄。那一年我在一个陌生的乡镇工作,除了生疏与漠然,我的全部热情所只能面对的,就只有书籍与工作了。
那时是秋天,那时是为了工作上的一个小小纠纷,我被迫站在高高的玉米堆上,面对几十张陌生的脸孔。年轻的心里没有经验一类的东西,烦乱与怒气填堵着我,尤其在对事情的原委糊里糊涂,而周遭却见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时。在我心中,充盈着无边无际的孤独,和由此而产生的悲壮感。
天旷,天清,云淡,云轻。那个时候,我仰首向天,如剑如芒的寂寥刺痛着我,让我绝望,便如在暗夜里,迷途于旷野,而身周便是阴险深沉的沼泽。
展开剩余72%那盏灯光便在这个时候亮起,我看到陌生的脸孔左右分开,然后我就看到我的朋友刘旭东,他走进人群。
那天我们携手走出人群,那些汹汹的陌生脸孔在那一刻变得肃穆,为我们让出路来。
天高地旷的秋风中,我随我的朋友,慢慢从绝望中走出。没有人试图阻拦我们,光明是一种纯粹的力量,它让邪恶辟易。
朋友是一盏灯,到今天,到永远,那双携我走出绝望的手,都给我前进的力量。
二
那是1991年,春末夏初,我与我的朋友一起登泰山。
当时由于生活中一件大不如意事,生活与心情,都处于有生以来的最低谷。四顾茫茫,只看到他人的漠然,看不见自己的路。就在极度迷茫中到了泰山,在泰山脚下一矿区,约上中学时的朋友王宏伟,同登泰山。
泰山的路,漫长多陡峭,这让我想起生活的路,想起迈步的艰辛。就在那一刻,无际的疲倦笼罩了我,我几乎丧失了继续攀登的力量。
那时我们已过了五大夫松,正走在十八盘上。极突然地,弥山大雾化成急雨,劈头盖脸下起来。
旁顾路周,没有避雨的地方可供我们两个人塞进去。一千几百米的高度上,我缩在狂乱的冷雨里发抖,感觉到的除了寒冷便是黑暗。
就在我几乎无力地坐到石阶上时,朋友拉了我一把:“既然没有地方避雨,我们就向前走。”
急雨冷风里,这简简单单一句话,如闪电,划过我心际。没有地方避雨,我们惟一的选择,就是继续走下去啊!
那之后,我们很快就攀到了峰顶。因为就在冷冷的雨中,朋友为我重新拨亮了心中那盏几乎熄灭的灯。
三
五年前的一天下午,我接到一封信,是一位不常见面的叫李培金的朋友写来的,告诉我他要参军了。
这是一位偏远乡镇偏远山村的朋友,贫困的家境、多病的父母令他中学未毕业就进了砖瓦厂。他在家中是老大,虽然身材单薄瘦弱,也理所当然地担当起维护家庭的重任。
他在信中说,他的父母想尽办法才让他参军,但他不想走,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逃避责任,且担心在部队干不出成绩。
读完他的信,我马上打电话问武装部,得知新兵第二天就要离县。我立即骑自行车,行10公里乡路,到县武装部,找到朋友。对坐半个多小时,我们相对无言,他只是倒出他挎包里的所有花生,一个劲地让我吃。
新兵们马上要开饭了,我告辞,他送我,一直送出去。大门外,我们站住,握他的手,我说:人生的关键处只有一次机会,抓住了,就不要放弃,离开了现在,就不要再回来。
松开手,朋友告诉我,这是他验兵合格后,惟一一个来看他的朋友,惟一一句对他的赠言。
走出很远我回身,朋友的手,一直扬在空中。
然后便是三年未有朋友的音讯。第四年起,我开始逐月收到朋友的信,信寄自北京某军校。
以心为火,点燃他人心中一盏灯的同时,温暖的也是自己。
一九九六年冬月
长
发布于:山东省